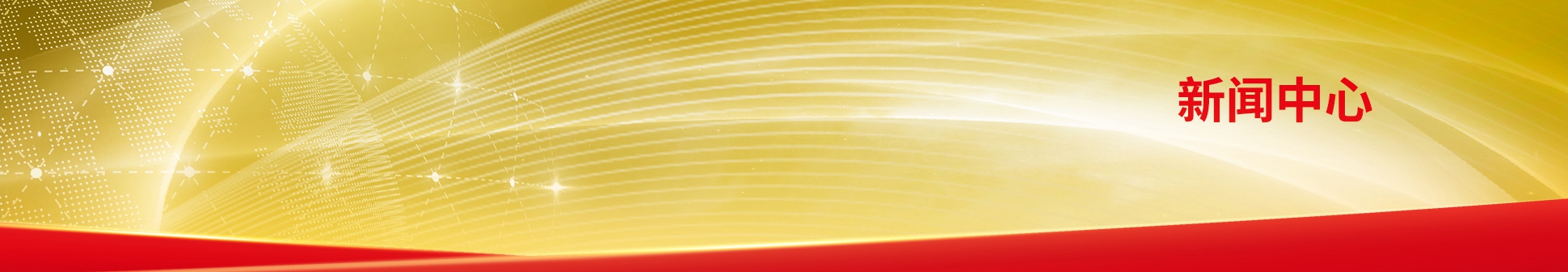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五角型”战略
1980 年代以来,我国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形成先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继之包括以蒙、疆为代表的西北角和以滇、桂为代表的西南角所共同组成的“ 五角型”战略格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作为“ 东部三角”,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具有当时的先发性、今天的成熟性和向内地的延伸性等特点。面向中亚的西北角和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西南角,具有后发性的特点,可以充分借鉴“ 东部三角”的先发经验,减少成本,少走弯路,形成“ 后发优势”。
二、开放大西南的战略意义
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已深度开放的形势下,加速开放西北角与西南角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这里主要谈谈开放西南角的意义。
从产业转移上看。我国由于自身的特点形成了“ 世界工厂”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由“ 东部三角”的体制与技术加中西部的资源与人力支撑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随着“ 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我国原有的人力成本优势将日渐趋弱,而“ 西部两角”的后发优势将日渐明显。未来十年,我国西南地区将成为与东南亚进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地,开放大西南可使西部在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从能源安全上看。为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需要建立缓冲地带。以石油为例,2009 年我国原油进口达2.04 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50%,其中80%经由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我国能源运输通道的“ 咽喉”,但南太平洋并不平静,安全存在隐患。中缅油气管道可以“ 截弯取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马六甲隐患”,于我于邻,于经济于政治都更为有利。
从外贸结构调整上看。目前我国对欧美贸易占比1/3 强(其中欧19%,美17%),加上香港转口因素则更高(45% 左右)。根据目前情况判断,未来十年,欧美对我出口需求增长有限,而东南亚、南亚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新兴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与这一地区贸易发展较快(占比达10% 左右),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45-50%),可以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带来极大的主动权。从战略上也可以说是以南南合作补南北合作,意义深远。
总之,我国大西南与东南亚、南亚有优越的地缘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应当顺应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加大大西南开放力度。
三、海陆通道与云南(昆明)定位
从产业结构的特点来看,当前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经济合作主要以第一、二产业加上少量高科技(与印度)为基础(大体类似1950 年代欧洲的“煤钢联盟”),经济活动主要以物流为主。因此,开放大西南需要建设高效率的产品集散中心和海陆空物流通道。从陆上(接壤4060 公里)通道来说,云南(昆明)事实上处于“ 南大门”地位,但以前主要是领土“ 南大门”,今后更要成为经济“ 南大门”,更要成为大西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从长远看,构建以昆明为内外连结点,南北(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万象-昆明-内地)贯通、东西(越南-中国云南-缅甸)呼应、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国际物流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古有南方“ 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近有“ 滇缅生命线”,可以预期,建立在和平与发展、开放与合作基础上的新兴西南通道,将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经贸大道。
四、开放大西南的金融思考
金融工作要全方位服务于开放大西南战略,可以从内外多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构建金融互助机制。在清迈协议框架下,可以确立一揽子信用额度,采取低息、中长期政府信贷等方式,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环境、教育和文化交流等事业;还可考虑以参股形式与当地政府共同开发,互惠互利。
第二,加强区域资金融通。初期可以以开发性金融(国开行、进出口行)为主导,商业性金融为补充,并可考虑与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进行银团贷款,并提供融资、汇兑、结算等综合服务,同时推动金融创新和区域市场培育。
第三,推进人民币“ 区域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应当是周边化—> 区域化—> 国际化。东南亚则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首选。为此,应当增强人民银行相关分支机构及有关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国际清算结算功能,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范围和规模,提升边贸金融服务能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同时鉴于西南的特点,要加强反洗钱及监管工作力度,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第四,建立区域金融联系机制与合作论坛。如可考虑建立大湄公河流域国家金融机构联系机制,设立大湄公河流域国家金融专家论坛等等,讨论区域内国家间的重大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和金融创新机制,促进金融信息、人才、技术、服务的交流与合作。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